
-
95年前,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引爆了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那天,3000余名北京青年学生为抗议北洋政府出卖山东权益,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率先点燃起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火焰。
- 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发端,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90年来,这团烈火熊熊燃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先进青年。
- 在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中国广大青年逐渐觉醒,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到了时代斗争的前沿,他们从封建家庭中走了出来,从课堂里走了出来,奔向社会,走向革命…… 青年的路,就这样越走越宽。
1919年,中国青年愤怒了,他们对现实政治彻底绝望,对上一代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进行否定,同时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抛弃了他们的父兄,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由于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知识分子在各式各样的西学中吸取养分,又将这些半生不熟,或者水土不服的理论应用在对病弱中国的临床治疗之中,动机未尝不好,心情却实在太过急切了。也正基于此,种种新鲜观念和学说泛滥成灾,种种思潮和流派粉墨登场,仿佛只要按图索骥,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尤其是在袁世凯病死,中央权威出现真空之后,中国政治重新退化到了四分五裂的乱世。知识精英们的“救世”之心愈发迫切,甚至屡屡显示出病急乱投医的姿态。
毫无疑问,这种心态带来了思想界的空前繁荣,也令对社会缺乏充分认知的年轻人的大脑烧得更热……
“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 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 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决心另起炉灶,去造就一个新时代。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1919年的7月,28岁的胡适在北京演讲时的说的话,胡适说:“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些青年厌倦了这个时代;厌倦了这个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部分青年们显然是等不及了,他们开始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4月11日,开国元帅罗荣桓之子、原二炮副政委罗东进,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做群众路线报告。凤凰湖北专访了罗东进中将,75岁的退休老人向我们讲述了父辈们的“社会革命”历程。
“在十大元帅中,我父亲是革命资历最浅的一个。年轻时候的父亲并没有想到革命,他一心想做的是土木工程师。那时父亲刚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国外都是高楼大厦,上海也是如此,他就认为搞建筑也许能为国家找条出路。”
1924年,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学土木工程。第二年,罗荣桓参加了青岛的反日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上了当地政府的黑名单。地下党为保护他们,安排他们南下。罗荣桓本来有机会上黄埔军校,但还是错过了。
“我父亲当时没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他又是近视眼,自认为不是当兵的料,还是想学土木,因此并没有想报考黄埔军校,而是介绍我六叔罗湘去了军校。他自己则继续报考中山大学,但是因为要考德语又没考取,只得又回了湖南老家。”
1927年,罗荣桓通过补考进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的还是土木。入学3个月,罗荣桓被派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不久就组织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罗荣桓担任党代表。这位书生没想到自己终究还是参了军,也没想到会在军队里干一辈子。
当时湖北很多地方都搞了秋收暴动,但大多失败了,罗荣桓领导的这一支走了出来,和武汉警卫团的一个连队合在一起,罗荣桓把队伍带到了修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这使他成为和毛泽东结识最早的元帅。

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一年,它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决心另起炉灶,去造就一个新时代。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它“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青年们在1919年用“少年中国学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彻底绝望,表达了对上一代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的否定,也表达了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抛弃了他们的父兄,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式微,则意味
- 着青年们对“社会改良”道路的失望和抛弃,意味着“改良”终于彻底失去了他的青年,青年们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革命”的道路——这年夏,中年人章太炎在他上海的书房里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即将成为中共党员的青年李汉俊则告诉芥川龙之介: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革命”,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终极信仰。

 到外面去 奔向社会走向革命
到外面去 奔向社会走向革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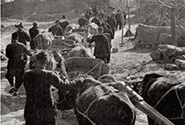 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先人后己 把青春献给祖国
先人后己 把青春献给祖国 知青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知青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人生意义大讨论 在迷惘中寻找自我
人生意义大讨论 在迷惘中寻找自我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