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写到:“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这或许可以借以形容当下80后青年的心理状态。在现实的洪流中裹挟向前,在坚守信仰与选择 庸常之间挣扎。不过,也有人替80后喊冤,冠以“奋斗的一代”,感慨他们生在这个高竞争、高压力的时代,出人头地要付出更多的汗水,活的比祖辈们更辛苦。
-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五四精神。新的时代、新的天地,五四精神应如何更好结合实际、契合时代需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1000多年前,范文正公的天下之责。“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500多年前,县官徐九经的为官之责。而“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这是60多年前,切·格瓦拉的革命之责。时代有时代的责任,个体有个体的责任。 80后说,谁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面对80后,有人说他们在蜜罐子里长大,身为独生子女心理脆弱,漠视社会责任,骄横跋扈;有人说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身处信息时代资源共享,更富有创造力,潜能无限。那么,在中国进入公民社会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80后青年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他们应该如何介入到社会公共领域,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凤凰网湖北频道专门采访了80后团干吴江,他出生于革命老区红安,17岁离家,在外闯荡14年。他回忆,刚刚改革开放那会,他的儿时,没人告诉他以后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理想未必就是一定从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做什么,而在于一种追逐理想的态度。
他说:“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常常把自己定义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我们更愿意将理想和现实靠的更近一些。奋斗的态度并不在于你去做什么事情,而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对于工作,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会为我的事业牺牲,但我们不会完全把自己给抛弃。”
在访谈中,我们感受到一代年轻人的不屈与奋进,思索着青春的价值和责任。
人的一生只能享受一次青春。青年时期就把自己的奋斗与国家、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联结在一起,将赢得永恒的青春。当这种人生追求成为一代青年的孜孜实践,迎来的,就是生机盎然的青春中国!

1980年,中国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80后这代人大部分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1980年,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思想重大转变以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关键节点,年幼的八零后懵懂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的童年伴随着物质与文化的多元一同成长,他们接触到广播、电视,间或有人在说什么学生闹事的事情,但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丝毫没有影响到80后们的日常生活。
80后念初中时,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体验不到这一历史对他们影响。80后们经历2003年的SARS事件,此时他们或在读中学,或被圈在大学里跳舞不准外出;再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所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的责任意识的确立。
- 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以上列举的种种历史事件已经证明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充满了戏剧和动感的,但是与"十七年"和"文革"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比起来,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
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席的一代。因为这种历史存在感的缺席,导致了80后面对历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一就是如大地震以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上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参与的高度的热情,在这样一种参与中,80后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暂时性"表明了这种存在感的虚无;这就是第二点,因为对于历史存在已经失去了信任,索性就彻底放弃了这种历史的维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这是在80后青年人中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倾向。

生理上的事实是,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在十年前也许不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今天需要特别严肃地提出来,因为经过30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
与80后的成长同时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 秩序中的全部降格。
在1970年代,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而自豪,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高唱"在那希望的 田野上"。但是到了200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对农民和工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嘲笑。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80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从起源开始,80后就不是在获得,而是在失去--"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全部世界"。
但似乎有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普遍实行和 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朴素的80后为自己摆脱了那些已经完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他们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面没有我们的田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
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在每一个8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是的,小资产阶级之梦 --至少在2009年以前,这个梦还不能说是白日梦,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理想和追求。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梦有些含糊,但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 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它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

 到外面去 奔向社会走向革命
到外面去 奔向社会走向革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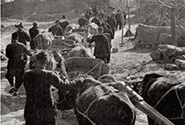 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先人后己 把青春献给祖国
先人后己 把青春献给祖国 知青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知青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人生意义大讨论 在迷惘中寻找自我
人生意义大讨论 在迷惘中寻找自我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